关于“空白”的几则故事,读后让人眼眶一热
人生空白亦为诗
■郑蜀炎
即便是不懂诗,但偶尔有诗句撞到眼里,心头也会山一重水一重的。
比如,读到这样的一首短诗:“希望有人给我写信/开头是:亲爱的/哪怕后面是一片空白/那也是我亲爱的/空白。”
当然,我要说的空白,不是纸墨文章间的笔墨疏淡、隐喻留白,而是人生际遇里的阴晴圆缺,岁月流逝间的意之难平。
一
有着温润如玉名字的黎秀芳,人生的开端也是烛影摇红。出生在南京秦淮河畔,作为千娇万宠的小姐,她的生活已被香车宝马、裙裾相拂填满。但是,在一片珠光宝气中,她却选择了“洁白的事业”——护理。
1936年,黎秀芳考上当时全国唯一一所护士学校——南京中央高级护士学校。上学才一年,日本侵略军就兵临城下。她随学校开始了凄风苦雨中的“流亡学业”。由于学习成绩突出,毕业时黎秀芳被留在学校任教。就在这时,她听到了共产党人吴玉章的一次演讲。吴老纵论抗战形势后,向青年人大声疾呼——到西北去,保卫建设我们的大后方。
理想的火焰一旦燃烧,便照亮了青春的道路。她与两个同窗好友几经周折,来到兰州高级护理学校,在黄河边开始了她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1949年初,黎秀芳的父亲专程来到兰州,想把她接走。但经过3天的慎重思索,黎秀芳坚定地选择留下。那天在机场送别时,父亲泪眼望断。不知是等待还是挥别的模样,成为父亲留给黎秀芳最后的记忆。
黎秀芳很快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解放军解放兰州接管学校后,发布的第一个公告就是让她继续担任已纳入西北野战军的兰州高级护校校长,其他同事也全部留任。
“护士必须有一颗同情心和一双愿意工作的手。”这是南丁格尔的话,也是黎秀芳对“洁白的事业”毕生的遵循。她在全国首次提出护理工作的计划性、科学性,创立了“三级护理”理论(即把病人分为危重病人、重病员、轻病员三级进行护理);她创造的“三查七对”“对抄勾对”等制度,奠定了中国现代科学护理的基础,一直沿用至今,被誉为我国我军护理事业里程碑式的成果。
她连续37年担任中华护理学会副理事长,相继被授予“模范护理专家”“全国模范护士”“国际医学成就奖”“医坛杰出人物奖”等荣誉。
1997年,她近乎浪漫的理想成为现实——黎秀芳获得了第36届“南丁格尔奖”,成为我军这一荣誉的首位获得者。
人生如此,称得上弦歌不辍、灼灼其华了。但是,我在采访中却发现一个空白——一路走来,黎秀芳一直是孤身前行,无伴侣相随。
她的遗嘱解答了我的困惑,也让我泪流满面:“我一生崇尚护理先驱南丁格尔,倾心致力于护理教育及管理,躬身耕耘六十载。效仿先贤,专注护理,我亦终身未婚,宗亲均居海外,膝下无一儿女,孑然一身,了无牵挂。故在我下世后,遂将平生所有积蓄全部捐赠医院,用于为部队伤病员服务。以绵薄之力,献仁爱之心,了平生所愿。并倡议业内有识之士,携手同心,共图护理发展之大业。”
陌上花开,缓缓归矣。
孤单吗?
不,黎秀芳的68位血脉宗亲送上这样的挽联:“黎氏家族,以此为荣”。
遗憾吗?
不,黎秀芳所捐平生积蓄设立的“为兵服务奖励基金”,今天仍在传承着“洁白的事业”。
黎秀芳遗体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如此耀眼、如此灿烂。是的,如果选择把一生奉献给挚爱的事业,生活中就会有一些难以顾及的缺失空白,但何妨将其视为生命之诗的省略号?捧读这样的诗篇,你能品味到诗韵丰沛、辞章瑰丽。你能领略到诗如其人,人如其名——秀美芳华。
二
专家考据,最早以“空白”入诗的,是宋人的“雪岭倚空白”。诗是写景,但我要说的是在皑皑雪岭,一个哨所里的一次时间空白。
无人区的定义是“没有人类常驻的区域”。当然,这是指生活者而不是守卫者。
上个世纪70年代,在西藏的一个无人区就驻守着这样的守卫者——边防连队的一个前哨班。
前哨,当然是远离后方、据守前沿的哨位。其担负任务的繁重、生活条件的艰苦,不须多言。风雪高原的时差和连轴转的边境勤务,加之近乎封闭状态的无人区没有什么参照物,更不巧的是,班里唯一的计时闹钟又坏了,这一下便误导了战士们弄错时间——把腊月二十九记为大年三十了。
哲学家说:时间并不在时钟里。同样,在战士们眼里,时间也不一定都在日历里。“除夕”既过,战士们又开始忙着执行边防勤务了。不过,大家总觉得有点不对劲。讨论了许久还是各执一词,最后决定向连部发电报求证——何日是除夕?
短短的电文让连长和指导员心里揪揪的、眼睛湿湿的。他们马上回复——今天是三十。军礼。
他们把年提前过了,拜年已晚,就致以军礼吧。
接下来的故事就顺理成章了:到了退伍时节,前哨班的老兵回到连队,连里专门为他们“补”了一顿饺子、几挂爆竹。
今天,现代化的后勤保障已经彻底改变了边防官兵的生活保障条件,但这一来一往的电报,成为连史室的重要收藏。
“雪里已知春信至。”可放眼天涯边关、哨卡边防,由于特殊的地理、气候和环境造成的空白故事还有许多,但此空白非彼空白,山河为证:有青春士兵热血,戍边男儿肝胆,祖国的边关,便永远不会留下任何的空白。
三
诗人可以把空白写得很美很浪漫,是望断天涯的“人归落雁后”,亦是咫尺眼前的“思发在花前”;是“孤帆远影碧空尽”,也是“青山有约定来无”。
不能否认的是,现实生活中即使是“有所期约,时刻不易”的笃定,也难免留下“遗憾聚散念几许”。
在一个海岛上,守岛的海防官兵把每年的台风季称为“探亲空白期”——每年这个时候,来海岛探亲的军嫂们常常受阻于台风,只能困在岛外。更让人揪心的是,船明明临近海岛,却因风急浪大而靠不了岸。离肠百结的夫妻隔水相望却不能相聚,挥手呼喊却不能相拥欢叙。茫茫海水滔滔浪,探亲假就这样变成了“望亲假”。尽管他们懂得“一家不圆万家圆”的道理,但一段“远在彼兮,旦夕以待”的空白,还是成为刻骨铭心的记忆。
1950年,人民解放军的先遣小分队在见不到一户人家、一缕炊烟的原始森林里走了7天7夜,翻越高黎贡山首次进入独龙江,让峡谷深处的独龙族人民,通过红红的五角星认识了共产党、新中国和人民子弟兵。
在此后的70余年时间里,边防部队见证着、参与着独龙族人民所经历并完成的两次跨越——从原始社会直接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再到实现了整个民族向小康的跨越。
为了完成跨越的使命,几十年间,我边防部队有8位烈士献身独龙江。限于当时的条件,有几位烈士牺牲前甚至没有留下一张遗照。因此,纪念馆和墓碑上只能看到令人遗憾的空白。
河山壮丽,岂能没有戍边人“在场”的叙事。据了解,当地政府正在通过各种方法,根据采集的形象数据,绘制烈士们的英容,弥补这样空白。当地领导说:“只要独龙江还在奔涌,他们的青春和梦想、姿容与笑貌,就不会被遗忘。”
艺术家对空白审美有很多理论,但在一个边疆村寨,我却从空白中品读出一种无声之念、无言之美。
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距边境线很近的一个寨子,地名拗口,但我一下就记住了——顺哈寨。寨子里有几排与傣寨风格迥然不同的青砖水泥平房,静静地映掩在凤尾竹间。时任乡武装部部长告诉我,这是原先边防某部前哨排的驻地,上个世纪80年代部队撤防后,寨里百姓定下个规矩:房子要好好守着,等着解放军再回来。他们记得家乡的谚语:虎去山还在,山在虎还来。
多少年过去了,老营房一直由傣族群众精心守护着——雨季到了,屋顶要补漏;刮大风后,院子要清扫……当年采访时,寨子里的一位老人告诉我:部队走的那天,大家砍了甘蔗、煮了鸡蛋堵在路口送他们。排长说不能收。我问他,儿子出门该不该带上妈妈的心意。解放军都哭了,我们也哭了。现在不哭了,只是想他们想得很呀。
又是许多年过去了,想来那老营房在军用地图上已经是一个空白的点位。但在我的记忆里,这里从来没有空白过,那些虎虎生威的年轻士兵们依然在小小的营房、热闹的傣寨中,留下“花花锦锦、活活泼泼”,有“无限声情,无限意味”。
野花红紫多斑斓,唯有寒梅旧所识。一切景语皆情语,雪中寒梅,茫茫之白,但彻骨之寒中有着沁脾之香……
文章来源:中国军网-解放军报
责任编辑:唐诗絮
相关文章
军地共建,让红色文物“活起来”
军史钩沉2022-01-27 13:22:58吉林省军地保护红色资源、传承英烈精神纪实
军史钩沉2023-04-19 09:36:37山东青岛军地做好革命老兵口述档案挖掘整理工作
军史钩沉2023-06-06 14:58:14时隔70余年的“团聚”,军地多方接力为“王团长”寻亲
军史钩沉2022-04-07 08:18:22“独胆英雄”魂归塔山丨军地携手助力老兵卜凤刚实现遗愿
军史钩沉2023-12-20 09:21:25萍乡市军地联合组织“重走秋收起义路”行军活动
军史钩沉2022-08-30 11:28:31海南万宁军地合力为烈士墓碑镶嵌彩色瓷像
军史钩沉2021-04-08 10:18:35军地连线缅怀志愿军一级英雄李家发
军史钩沉2022-04-11 12:58:17新修订的《烈士安葬办法》施行后,山东省军地联合推进“慰烈工程”
军史钩沉2023-04-04 09:15:53江苏省徐州市军地举行纪念淮海战役胜利73周年仪式
军史钩沉2022-01-18 10:31:25
军情热议
以武谋霸:美大幅增加军费,备战高端战争
近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为美军新一财年的建军备战提供资金支持和政策指导。与...日本新潜艇将实现对陆打击,加剧地区军备竞赛
近日,日本川崎重工集团公布下一代常规潜艇设计方案,旨在取代自卫队目前装备的大鲸级。新型潜艇将突出“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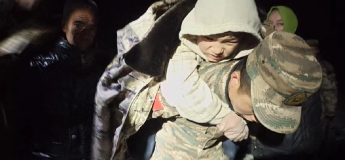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28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28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