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九口堰
寻找九口堰
■程文胜
一
湖北省随州市古称“汉东之国”。这座城市曾深藏着炎帝神农的耒耜桐琴、春秋战国的编钟鹿鹤、唐宋大家的金声玉振、大夏王朝的风起云涌,当然还有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游击的苦难辉煌。
也许是30多年军旅生涯累积的习惯,相比深藏于斯地的古代灿烂文化,我更愿意追溯新四军第五师的历史源头。翻阅《新四军战史》,当我读到新四军第五师“长期远离军部、孤悬敌后”几个字时,心潮翻涌,脑海顿时展现第五师官兵在日寇、敌顽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苦心孤诣建功立业的历史画卷。
提起新四军第五师,随州本地人会介绍一个地名:九口堰。这是随州市曾都区洛阳镇的一个村落,那里有一处明清时期古建筑——孙家大院,第五师当年即在此宣告成立,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九口堰新四军第五师革命旧址纪念馆也坐落于此。
地名从来都是一个浓缩地域文化、承载精神信仰、彰显历史遗迹的符号。比如罗霄山脉中段的宁冈、遂川、永新、酃县、茶陵等地名,就镌刻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建成的光辉足迹。我由此相信,九口堰也见证了新四军第五师的创建和发展。可是,当我查遍战史中关于新四军第五师的成长轨迹和大小战斗,没有找到当地人津津乐道的“九口堰”。
《新四军战史》由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6月公开出版。按说,九口堰这一地名的出现远早于编纂时间,战史在叙述新四军第五师包括其前身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创建抗日根据地时,不可避免会提及一些地名,应该不会遗漏九口堰。为此,我曾问询当地文化界的友人,他们也一头雾水。这更加激起我寻幽探源的历史兴趣。
我将《新四军战史》中与第五师标志性事件相关联的地名一一梳理标注:1939年11月,第五师前身——豫鄂挺进纵队在应山以北的四望山统一整编,随后至京山马家冲。12月5日,日军第13师团一部1500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闪击马家冲,纵队胜利突围,安全转移至京山八字门。1940年3月,纵队在地处鄂东礼山、孝感两县边界的大小悟山与顽军程汝怀部激战,击溃第19纵队第3支队等部2000余人,控制了大小悟山地区,“边区党政机关及纵队指挥机关随之进入这一地区的黄家冲和姚家山”。6月5日,国民党第7军张淦的两个师和程汝怀部两个纵队2万人分路进击,纵队被迫撤出大小悟山,分别向赵家棚、大山头、八字门转移……
四望山、马家冲、八字门、黄家冲、姚家山、赵家棚、大山头……这些质朴的地名宛若一颗颗珍珠,串起第五师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而“九口堰”缘何不见踪迹?
二
从常识的角度看,九口堰的地名不见于战史,极有可能是地名的历史称谓异化或当时行政区域划分不同。九口堰或许只是当地人对自然地貌的概括,比如十里棚子、三岔口之类。九口堰大约就是九口堰塘的代称。
据当地人介绍,九口堰地名的出现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叫孙家大湾。此地以前的确有大大小小相连接的堰塘,其中九口堰塘较大。站在山顶俯瞰,九口堰的一片水系如同一条健步行走的虬龙,显示出铿锵澎湃的生命活力。至于为什么从孙家大湾改为九口堰,当地人更是语焉不详。
九口堰地名来源含混不清,地理方位却具体明确。我找来一张大比例地图,对照战史勾画历史脉络,以红蓝铅笔标明敌我态势,九口堰的军事要冲价值一目了然。
九口堰位于白兆山脉中段东北麓,白兆山是大洪山向东延伸的支脉,地跨随县、安陆、京山等县市,在抗战时期是控扼随枣走廊的东大门。新四军第五师就是我党打入敌后的一枚楔子。
1939年1月,新四军派遣一支160人的队伍从河南竹沟南下豫鄂边区,开展豫鄂边区的抗日游击战,并在四望山创建抗日根据地。这支队伍就是新四军第五师的源头——独立游击大队。
独立游击大队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当地党组织配合下,不断会合当地抗日武装,聚少成多,渐有规模。当年6月26日,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在湖北京山养马畈成立,李先念任司令员,被毛泽东同志称赞为“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的女革命家陈少敏任政治委员。
风雨如晦的岁月,步步惊心的境地。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很难想象,孤立无援、时刻面临生死抉择,坚持活下来已属不易,如何还能与日伪作战、与敌顽周旋,建立稳固的根据地?
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力掀反共浪潮,鄂中地区日伪敌特遍布,我抗日力量一有风吹草动,敌伪便集合兵力“围剿”。当豫鄂独立游击支队进入京山崖家冲、上老冲一带时,敌伪即得知消息,从京山坪坝、宋河、安陆等地兵分3路分进合击。伪军进至冲口槐树湾时,被我哨兵及时发现,鸣枪报警,李先念率部突围,躲进山洞,藏身5日才得以脱险。
多年以后,李先念重回故地时说:“那时生存发展压力很大,我从30多岁就开始失眠。睡不着觉就爬山,爬一二十里,爬完山天就亮了,洗把脸就开会研究敌情。”
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屡遭敌袭,随即转战随南,在白兆山一带对敌伪打击、驱逐,逐步扫清白兆山外围,同时整编扩大队伍。
《新四军战史》《新四军文献》等正史多次提及的“随南”,只是一个大体方位。九口堰这一历史坐标,则多出自随州市新四军研究会整理的第五师老领导的口述。当然,口述历史一旦与遗迹实物相印证,同样具有说服力。
三
被围困的日子无疑是艰难困苦的日子。国难当头,即使处境窘迫、步履维艰,新四军指战员也要坚持抗战直至胜利。
尽管如此,国民党顽固派仍想拔掉新四军这根心中之刺。1941年1月,皖南事变的枪声惊醒山林,震惊中外。
皖南事变后,遵照中央关于迅速组建新四军第五师的指示,李先念于1941年4月5日发出《率新四军第五师全体将领就职通电》,宣告豫鄂挺进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4月10日,第五师机关、驻白兆山的第十三旅和第一纵队指战员,在孙家大湾前河滩上召开整编誓师大会,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
第五师活动于武汉四周,地跨鄂、豫、皖、湘、赣5省边区,如果没有听党指挥的忠诚、抗战必胜的信念、不怕牺牲的勇敢、与敌斗争的顽强,不可能在战斗中发展壮大。在第五师成立前后近3年时间里,孙家大湾始终是豫鄂边区抗日游击的指挥中枢。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孙家大湾就在如今的九口堰村。
时任第五师政治部主任任质斌回忆说:“1939年冬到1945年8月日寇投降,无论是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还是新四军第五师,我们的司令部一直驻扎在两个地区:在京汉铁路以西,住在随南白兆山,包括京山的大小花岭;在京汉铁路以东,就住在鄂东的大悟山。特别是从1939年冬到1942年6月,对第五师建设起着重要作用的关键时期,我们纵队和第五师的司令部一直设在白兆山的中心地带——洛阳店的九口堰地区。”
白兆山方圆百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九口堰深入腹地,进可扼要道,退可避深山,军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正因如此,敌顽屡屡进犯。当时,李宗仁集重兵进攻豫鄂边区,先后出动12个师达10万之众,对第五师发动全面“清剿”。白兆山抗日根据地被敌“蚕食”,新四军第五师分布各地,驻九口堰机关和部队处境更趋艰难。为保存力量,1942年6月,第五师不得不撤离此地。
九口堰新四军第五师革命旧址纪念馆展示的一份作战文书称:“自顽军开始向我大举进攻以来,我曾集结主力数度奇袭,企图以各个击破的战术,打破此次‘围剿’。每次作战虽获小胜,但因各种原因,均未实现原定计划,伤亡减员已达千人,后方补给亦极困难。”其时,敌强我弱,为避其锋芒,第五师审时度势奉命战略转移的举措是正确的。
1942年7月21日,因新四军军部和第五师联络中断,不便指挥,中央军委根据新四军军部建议,决定第五师由军委直接指挥,建制仍归新四军。第五师除留一个旅作主力外,其余均地方化,建立5个军分区。
第五师在一次次胜利和失利中正确总结经验教训。两年后,第五师挥师随南,一举收复白兆山根据地,第五师司令部、政治部又一次进驻孙家大湾。
第五师再临九口堰,这一天是1945年4月11日。
按照第五师领导人物传记和回忆录中的说法,第五师成立后指挥机关驻扎在九口堰的时间最长。当然,老同志口中的九口堰,只是一个今日方位名词。对人们而言,无论叫什么名字,那片热土都是一个永恒的坐标。它如同夜空明亮的星辰,闪耀着让人不能忘怀的历史光辉。
正当我为九口堰这一地名困惑不已时,与一位学者讨论文化话题其间,我顺便提起九口堰。这位学者说,早些年曾听过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丁凤英的讲课,记得她提到九口堰地名的来源——丁凤英一行曾拜访过新四军第五师首任师长李先念。李先念对她讲,他还记得司令部驻地那个湾子有九口堰塘。随后,李先念便拿起笔在一张报纸的空白处写下“九口堰”。
责任编辑:唐诗絮
相关文章
军史钩沉
军史钩沉2022-04-14 16:48:38军史教育路上“追光者”
军史钩沉2023-01-10 10:57:25军史瞬间
军史钩沉2024-04-01 11:34:10每名党员都是党史军史书写者
军史钩沉2021-02-01 11:04:50从党史军史中汲取奋进力量
军史钩沉2024-12-12 09:35:07用军史学习教育滋养战斗精神
军史钩沉2024-07-05 09:06:14图文军史馆
军史钩沉2024-04-01 11:34:48军史馆里忆往昔励斗志
军史钩沉2022-09-28 09:51:41军史文物|《战伤疗法》
军史钩沉2023-02-17 15:55:17军史组歌《从南昌走来》:穿越时空的奋进乐章
军史钩沉2023-08-24 15:32:02
军情热议
日本开发反卫星武器,推进太空军事化
当前,日本正从多维度体系化构建太空军事能力。据日本媒体报道,防卫省近日发布首份太空军事能力建设指导性...美军针对中国编织多域情报监视网
美军将印太地区视为“战略竞争核心战场”,正通过构建全域情报收集平台,服务于其霸权利益。从2月美军印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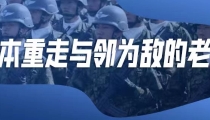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28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28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