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槐树下的故事
■乔秀清
儿时的记忆里,我家门前有棵老槐树,谁也说不清它是什么时候栽的。老槐树的树冠高过了房檐,树干粗得一个人伸开双臂也搂不过来。槐花盛开的时节,醉人的花香飘散,使生我养我的村子香气弥漫。
夏天,冀中平原滹沱河畔烈日炎炎。我家门前那棵老槐树下,是乘凉的好地方。奶奶坐在蒲团上摇着纺车,嗡嗡的纺车声和树上连绵不断的蝉声,汇成了乡村夏日的乐章。我坐在微凉的地上,听奶奶讲故事。小伙伴们也一个个光着膀子,到老槐树下凑热闹。夏天有多长,纺车上的线有多长,奶奶讲的故事就有多长。
奶奶讲的都是抗战时期发生在她身边的事情。她说,自日本鬼子来了,烧杀抢掠,老百姓一天也没安生过。一提起鬼子,大家都恨得咬牙切齿。村里的小伙子都铆足了劲,要跟鬼子拼到底。
奶奶告诉我,我爹担任了村青年抗日先锋队主任,带领队员们配合县大队火烧鬼子的炮楼,阻击敌人的运粮队,捉特务、除汉奸。我娘担任了村妇救会主任,带领妇女们给八路军做军鞋、缝军衣,动员青年参军上前线,一天从早到晚忙得脚跟打后脑勺。
“记得那是1940年夏,我正在树下纺线,你叔光着膀子回家,取了一件粗布褂子披在身上,对我说,娘,我参加八路军了,等赶走鬼子,我再回家看你。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心里扑腾扑腾跳得厉害。”奶奶说。
她叮嘱我叔:“你上前线打鬼子,娘不拦你。可是,娘担心呀。方便时,给娘捎个信,报个平安。”
“嗯。”我叔留给我奶奶一个字,扭头就走了。几个月后,奶奶才听说,我叔跟随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反“扫荡”,打了不少胜仗。
奶奶摇着纺车,把她饱受的苦难也摇了出来。她说,那是秋后的一天,汉奸领着鬼子窜到我家,把房檐上晾晒的几十捆高粱穗子扔到地上,一把火烧成了灰。一个日本兵用刺刀,将猪圈里养的那口猪捅死了。汉奸和鬼子生拉硬拽地把她弄到院子里,逼她说出我爹、娘、叔的下落。
奶奶说:“不知道。”
汉奸把奶奶推倒在地,两个鬼子一个用枪砸她,一个用脚踢她。这时,附近传来一阵枪声,敌人才匆匆离开。
炎炎夏日,我见奶奶讲故事口干舌燥,便提上家里那把锡壶,拴上麻绳,到村东头的古井边,往壶里装满清凉的井水,倒进碗里端给奶奶喝。
奶奶喝了几口井水,对我和小伙伴们说:“我再给你们讲讲鬼子大‘扫荡’的情况。”那次,鬼子不少人马来势汹汹进了我们村,挨门挨户地搜查共产党员、村干部和青年抗日先锋队成员。因汉奸告密,鬼子包围了村支书家,并且找到了地道口。村支书就藏在地道里。后来,鬼子弄来一堆柴火,放在地道口。烈火熊熊,浓烟滚滚,藏在地道里的村支书活活被熏死了。“据说,县城里的抗日烈士纪念碑上刻着他的名字。他的学名叫什么,俺不知道,俺只记得他的乳名。”奶奶说。
滹沱河边刮来的风,吹得槐树叶子沙沙响。“好舒服!”奶奶不禁感叹。紧接着,她又开始讲我爹脱险的故事。
奶奶说:“那个夏天,你外公出事了。他担任谷家左村的维持会会长,日本鬼子察觉他暗地里为共产党办事,就将他扔进了猪圈里,企图用土坯将他砸死。鬼子撤离后,气息奄奄的他被乡亲们救了出来。几天后,你爹悄悄去谷家左村看他。没料到,遇上了进村的鬼子。他蹲在地上,假装磨剪子。一个日本兵伏在他后背,哇啦哇啦地说了几句听不懂的话。你爹猛劲将那日本兵从头上甩了出去,撒腿就跑。路上,他远远望见咱们村火光冲天,断定是鬼子进村了。他琢磨这会儿回家不安全,便在野地里的一个瓜棚待了一夜。天刚亮,你爹醒了,听见了几声马叫。原来,一群鬼子正在附近吃早饭,几匹马在吃草。你爹撒开腿,拼命地跑,幸运地在鬼子眼皮底下逃走了。”
多年后,爹领着我扒开屋里墙壁上的两块砖,从墙里取出一个包裹,对我说里面的东西要上交。那包裹里竟藏着一把匕首和一颗手榴弹。爹说,这是当年组织发给他的自卫武器。我望着那把匕首和那颗手榴弹,不禁在脑海中想象起父亲打鬼子时威武的模样。
又一天,雨后初晴,老槐树下落了一地淡黄色的槐花。奶奶让我用扫帚扫出一片干净的地方。她又坐在蒲团上一边纺线,一边给我讲故事。
我问奶奶:“你见过县游击大队大队长王东沧吗?他是一位抗日英雄。”奶奶说:“俺没见过王东沧大队长,但听你爹讲过他的故事。1944年正月,王东沧带领40多名游击队员,抢渡滹沱河,向南突围。因河面较宽,河水流着浮冰,渡河非常困难。一位老乡跳上冰块,去河对岸弄来一条小船。队员们交替乘船到达滹沱河南岸抗击敌人。在王东沧的指挥下,县游击大队的指战员多次击退敌人。天黑突围时,王东沧等9名指战员光荣牺牲。”
奶奶给纺车上添了一缕棉絮,摇着纺车接着说:“我见过县游击大队政委张根生,个子高高的,人很精神,以前在咱村隐蔽过。新中国成立后,他走上领导岗位,还抽空来咱们村看望保护过他的老百姓……”
奶奶的话,让我想起大雨滂沱的一天,我家院子的地面塌陷了一个大坑。我问奶奶咋回事,奶奶对我说,这是当年你爹和你娘挖的地道。敌人进村“扫荡”,青抗先、妇救会的同志们,都在咱家的地道里藏过。
孩童时的我,听奶奶讲了一个个血泪故事,从骨子里恨透了鬼子。18岁那年,我怀着保卫祖国和人民的强烈愿望,光荣参军入伍。离开家乡那天,天空飘着雪花,母亲送我到村口。这位在抗战时期把一批批青年送往前线的妇救会主任,送自己的儿子参军时,却站在村口久久不肯离去。爹骑自行车载着我,赶了40里路才到达新兵集结地。我曾写下这样一首小诗《那一刻,父亲呜呜哭了》:
我站在县城的道路旁/送父亲踏上归途/平原的风托住了欲坠的夕阳/也吹开了我心灵的窗户。
爹,天就要黑了/回吧,还要走几十里路/放心吧,到部队,儿一定好好干/不给爹丢脸,行不。
那一刻,爹呜呜哭了/当年铁骨铮铮的青抗先主任/为何泪湿黄昏,如此动容/是激动,是喜悦/还是难分难舍/我至今也说不清楚。
在军营里,我经常在梦中听到父母的叮咛和家乡滹沱河的浪涛声,看到冀中平原燃烧的抗日烽火。近几年,我回家乡探亲,和几位朋友来到了县游击大队大队长王东沧牺牲的地方,瞻仰了王东沧烈士之墓。我和县游击大队政委张根生的儿子张志奇多次会面,一起回顾我们先辈在战争年代度过的艰苦岁月,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如今,抗战胜利已经80年,奶奶和爹娘都离开了人世,我家门前那棵老槐树也不见了。老槐树下的故事,却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
作者:乔秀清
文章来源:中国军网-解放军报
责任编辑:唐诗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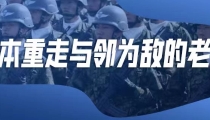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28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28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