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被软禁后的一次曝光
该文见报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反响,在政坛也引起不小的震动。甚至有人猜测,是不是蒋介石对张学良的囚禁政策有所松动?
最近笔者在翻阅有关张学良的资料时,找到两处有关莫德惠探视张学良的记载。第一处是在张学良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记有“本月十五日,莫柳忱(即莫德惠)来寓探视,由处长李肖白陪同,带来家人及朋友信件多封跟亲友赠送的甚多物品。莫在寓小住五日,谈话时李(肖白)、刘(乙光)常是在座。彼告余之东北人寄予我的热情,使我感激而惭愧,心中痛快而又难过,不觉眼泪流出。……”
第二处是在张学良给蒋介石的信(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九日)中,也记有:“莫柳忱(即莫德惠)先生奉命来山,述及钧座爱护良之深情,一如往昔。……除将良一切日常生活及读书情形详告莫先生外,兹略为钧座一陈:十年以来,良涉猎书籍门类甚广,自从病后,专以明史为目标,一切文艺掌故,皆为明代为着眼。本想研究明清两代史,又恐涉及过广,先未敢存此奢望。……”
据已故多年学者张魁堂曾引用张潜华的一篇未刊文稿说,此次莫德惠探视张学良负有特殊使命,且有资料证明:“莫氏经蒋特许,到天门洞后,单独与张学良谈话(不准负责看守的刘乙光及李肖白等人旁听),告诉张,说将要给他自由,但是有三个条件。一是要张学良承认西安事变是上了共产党的当;二是要交出“九·一八事变”时蒋给他的不抵抗电报;三是释放后必须出洋。张没有答应蒋的条件,莫氏无功而返。”因此,莫德惠的这次探视,备受各方关注。
《大公报》重庆版记者是如何采访到如此重要的独家消息?就连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和《中央日报》也感到奇怪和不解。
2005年12月11日,张学良将军的大型塑像矗立在沈阳张氏帅府博物馆广场。该塑像高7.2米,由沈阳鲁迅美术学院张秉田教授创作。张学良将军生于1901年,2001年10月15日在美国去世,享年101岁。 中新社发 刘宝成 摄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四六年四月初,《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一九○一至一九八○年)从陈布雷(一八九○至一九四八年)处获知,东北元老派人物莫德惠(一八八三至一九六八年)将于近期赴贵州桐梓探视被软禁十年之久的张学良。陈布雷对王芸生一再强调,这次探视是经过蒋介石批准的。
此时,王深感此事之重大,琢磨着一定要设法报道出去。恰在这个时候,《大公报》的管理中心由重庆迁往上海,王芸生四月十一日离渝赴沪。行前,王专门找到《大公报》渝版记者高学逵,布置待莫德惠探视张学良后的采访和报道工作,嘱咐他此事绝密,并留下一封致陈布雷的亲笔信,请他写完稿件后,交陈审阅。王芸生把这次采访和报道任务交给高学逵是经过周密思考的。高学逵于一九四○年进入《大公报》后,因专事采访战时的后方新闻,与各方面交往甚深。
莫德惠,吉林省双城人,天津政法专校毕业,曾任北洋政府农商部次长、东北大学校长、奉天省省长,还任过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考试院院长等职。莫德惠是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五日由重庆抵达贵州桐梓的,四月二十日返渝,与张学良朝夕相处五天,倾心交谈。莫德惠回到重庆后,《大公报》渝馆记者高学逵立即前往他休养的仁爱堂医院对其进行了采访。
高学逵见到莫德惠后,急切地问:“你这次探视张氏如何?”莫说:“这次获得蒋主席的特许,并派了一位处长陪同我去了一次贵州的桐梓乡间一个湖上探视阔别了八年的张学良氏,在那环境幽美的湖畔,我们共同生活了六天。在那几天里,除了谈些读书与生活之类的事情外,我们彼此都以一种轻快中带着沉默的情绪来表露自己的心境。”莫氏的情感是丰富的,在平时他每次跟青年人谈到旧事,或者东北问题,都感慨万端,常常老泪横流。这次与记者谈话,他却没有像过去一样的动感情。但他那有着毛病的眼眶里,老是潮湿着。
资料图:2005年9月19日,为纪念千古功臣张学良将军而修建的少帅陵,在张学良将军出生地附近鞍山市台安县西平森林公园落成,张学良在天津的亲属专程赶来参加衣冠入葬仪式。“少帅陵”由功臣坊、正门、纪念堂、衣冠冢和少帅碑林5部分构成。少帅陵将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旅游观光基地和对外文化交流基地。 中新社发 赵益飞 摄
开始谈话的时候,莫德惠首先回忆着八年前的往事,说:“我跟汉卿已经八年不见面了,这次见到了,汉卿说我的胡子斑白了,而我觉得他胖了很多。”“卢沟桥事变”前一年,莫氏曾经好几次探视过那时居留在蒋主席的故乡──溪口的他的老友张学良,那时还没有战争,要探视张氏还相当方便。后来战争把人与人之间隔绝了,这次是战争结束后,张氏第一次与莫氏接触。“从一九三七年起到今天,整整十年了,”莫氏叹息着说:“十年的光阴,汉卿的全副精力完全放在书本上,由于环境上的变迁与感受上的变化,他读的书籍跟着他所要追求的真理,也在不断的演变,这十年来他读书的演变是进步的。”根据莫氏所述,这十年来张氏所读的书籍达二百余种,同时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来说明他读书演变的过程。
莫德惠耐心地对记者介绍着。他说,张氏读书的第一个时期:“在汉口时,蒋主席为了教育他,特别请了一位姓步的老先生给他讲解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从那时起他开始接触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思想。对中国的旧文化也有了相当认识。后来战争把他送到了后方,更使他离开步老先生而接触到许多实际问题。”
“他第二期的读书生活,是在由溪口内迁途中,与最基础的农村社会发生了关系以后,对农村经济生活感到了兴趣,并体验到国民经济的重要,从此,成为解决社会问题最基本学理的经济学,又成为他研究的中心了。到息烽乡间以后,他就开始了这一门学问的研究。为了深一层了解在经济学上所引用到的哲学的诸问题,他又选读几种哲学书。又由于学习种菜、采茶、养鱼、养鸡,对自然科学的书籍亦有相当研究。这个时候,使他懂得了事物变化的一定的规律是怎样的。”
张氏读书的第三个时期:“三年前是战争到达最艰苦的年头。他从报纸的舆论上看得出国运的险恶,根据他所知道的事物变化的道理,他开始研读中外历史,希望在历史上找出一些解答现实问题的道理。他更注意到明朝是怎样兴盛起来,及后又为什幺亡给清朝的前因后果。这之后到现在,他一直在从事明史的研究,最近又读些民族学的材料。他希望得到更多的关于明代史事的资料,使能作更深一层的探讨,并想从事于历史著作。
莫德惠还给记者提供了一张书单,上面开列着一串张氏读过的书名,从中可以看到张对于历史书籍的涉猎相当广博。这份书单开列着以下书名,其中有:中国近代史(大学丛书)、中华两千年史、清代通史、中国通史、东林始末,三朝野纪、中国史论集、清代文献纪略、东北通史、国史大纲、明儒学案、船山哲学、使琉球录、明武宗外纪、东南纪事、中国政治思想史、明季政治与社会、行边纪闻、边政考、安南图志、刘宗周年谱、南明忠列传、中国伟人传、张居正评传、船山遗书、王文成文集、明季北略、明季南略、西域行程记等四十二种。
接着,莫德惠又向记者介绍了张氏的家庭情况。
资料图:2005年9月9日上午,张学良的儿子张闾琳、儿媳陈淑贞、孙子张居信一行专程来到西安张学良将军公馆。张闾琳回到阔别68年前父亲和自己住过的房间里,思绪万千。 中新社发 侯智 摄
他说:“十年来追随着张氏过着这种幽居生活的是一位美丽而贤淑的赵四小姐。她写得一手好字,这是十年来的一点收获。她经常替张氏抄录笔记,有时候也作两首诗消遣。她对张氏生活上学习上帮助很大。她是张氏唯一的慰藉。张夫人于凤至女士领着四个孩子远居美国,大儿子及次子、女儿都结了婚,三公子还在学校念书。”
记者还请求莫氏详尽介绍他与张氏朝夕相处的情况。莫说:“在湖上,张氏的日常生活是简朴而有规律的。每日的起居照例是:六时起床,七至八时之间用早餐,九至十时钓鱼,十二时吃午饭,饭后稍睡片刻,下午三时至四时钓鱼,有时打猎(水鸭),其余的时间就是阅读书报,晚九时休息。
在美丽的湖上,已经侵蚀了他已有的生命上六分之一的春光,每天在湖畔垂钓的时候,面对着碧绿的湖水,静思着,丝一样的波纹,时常牵动了他的心绪,作着沉长的回忆。”
“因为在乡间物价低廉,张氏又能参加劳作,自己养鸡种菜,日常食物营养很好,尽管喜欢运动的人,现在因为没有玩球的环境,但身体却是很健康的。”
记者还记述了莫氏给他看的三张照片,这是三张珍贵的纪念品。一张是湖心划小船时照的,另一张是在湖畔照的,第三张是在野外照的,均有张氏钢笔题字。莫氏拿着这三张照片,若有所思地说:“从照片上看,过着十载的幽居生活的张氏,面容虽然不减当年的丰满,然而脸上却带着非常沉重的忧思,仿佛有着什么心事似的?”
高学逵采访后,迅速把莫德惠所述撰写成文,并手持王芸生的亲笔信找到陈布雷。
陈布雷吸着烟,审看着稿件,一句话没说,就把稿子退给了记者。就这样,一篇采访张学良的稿件通过了审查。这时,高学逵接通了上海的长途,向王芸生汇报了访莫稿件已经通过了审查,王指示立即见报。
这就是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张学良的生活》一文在《大公报》重庆版发表的缘由。
王芸生观察了两天,没有看到蒋介石处有太大的动静,遂安排二十九日《大公报》上海版转载了这篇专访。
(来源:香港大公报 作者:王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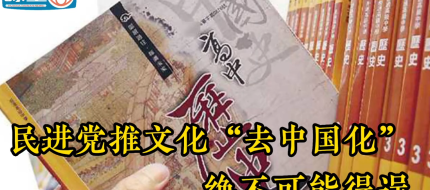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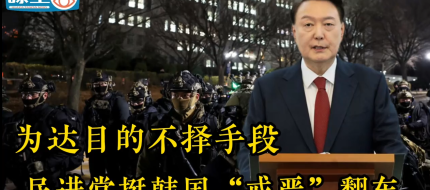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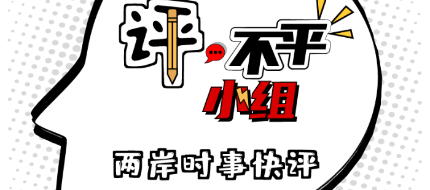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28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5281号